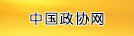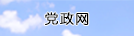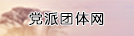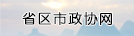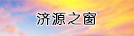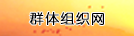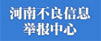【乡村记忆】我在济源塘石的知青生活
撰写时间: 2025-02-25 来源: 济源日报张林春
1974年4月,我们这批焦作的初中、高中毕业生刚刚走出校门,就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,胸佩大红花,怀着骄傲和激动的心情,乘坐卡车来到了豫西北的济源县克井公社塘石村。我们一行26人,女生中,最大的王秀荣19岁,最小的刘延不到16岁。男生中,最大的原永生18岁,最小的闫玉喜不到16岁。我17岁半。此前,按照政策要求,我们的城市户口和粮食关系都已被迁入济源克井派出所和原昌粮站。第一年由国家供给粮食,以后我们就要在农村插队落户自力更生了。如果不是1978年到1979年政策改变,知青返乡回城,我们中可能有不少人会在济源农村劳动生活一辈子。
从整体上来看,我们下乡插队到济源塘石的知青算是幸运的,政治教育、文化学习、劳动条件、生活条件、安全保障以及当地的民俗民风都相对较好,那几年的知青生活让我们受益匪浅。
一、第一印象
1974年的农村实行的是公社、生产大队(大队)、生产队(小队)三级组织架构,和现在对应,公社相当于乡镇,大队相当于村,生产队相当于居民组,农民叫社员。那时,塘石村总体上是以生产队为劳动单位的集体所有制,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分配方式。社员们集体种地收粮、种树收果,家里可以养鸡养猪,吃菜是队里的菜地分菜。大队不靠山不靠水,没有像样的副业和商业,代销点、医疗所、小磨坊等零打碎敲,挣不了多少钱。大队的果园、砖瓦窑、毛笔厂等,由于规模较小,收益也有限。每年收获季节,各生产队要按公社、大队分配的指标,上缴公粮(农业税),还要留提留(钱或粮)。除了卖余粮和搞副业有些现金收入外,大队、小队、社员们的手中,基本上没有多少积蓄。社员们生活都比较简朴,穿戴也显得土气。家家户户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,没有说哪家多富,哪家多穷。
每年,县里、公社都要搞工程建设,像挖河道、修水坝、整梯田、植树造林等,都要各大队组织出工出钱。这些都是公派的,无论是钱财和人工,还是生产工具等,都分摊到各大队,社员们出义工,吃、住和劳动工具什么的都需要自行解决。因为我们青年队是下乡锻炼的知青,又都是单身,所以只要有工程建设,大队都要安排我们去参加。虽然吃得不好,住得不好,干活也劳累,但是我们很愿意和社员群众一块干活,跟着他们学习劳动。
二、难忘的冬天
下乡当年的12月,公社组织我们这些知青集体到克井公社石河大队去整修“大寨田”。那是靠近太行山的一大片北高南低的山坡地,要垒砌田堰,平整地块,搞成一块块的“大寨田”。我们都在石河大队住宿、搭伙,由于地方小、人多,我、程胜利等三队的10个人,被分配在一间很小的民房里。打扫了一遍卫生,弄些麦草铺在地上,再铺上被子,就算有了睡觉的地方。
第二天天不亮,领工的大队干部闫黑留就挨着门叫醒大家。吃完早饭,我们就拉着平车,带上工具去山坡上干活。工地上插着红旗,挂着标语,响着宣传鼓劲的大喇叭,传出高亢的口号声,漫山遍野人头攒动、车马穿行,一派战天斗地的劳动景象。冬天气温较低,土地冻得十分坚硬,用铁锹挖很费力,用铁镐刨会震得手臂发麻。但是,因为我们知青是初次参加这样类似“革命运动”式的开垦建设,所以大家都情绪高涨,兴致勃勃。
早上天不亮就出工干活,中午吃过饭接着干,下午日头落山后才收工。劳动时间长、强度大,晚上又休息不好(经常是半夜起来解手后再回到铺前,就没有了睡觉的地方,只能是硬挤进去侧着身子睡),所以身体渐渐地有些吃不消,加上干活时出力流汗不注意,受冷感冒的事时有发生。一个多星期后,我和高树芳等几位同学就受凉感冒,头晕目眩,干不成活了。大队干部闫黑留知道后,就嘱咐我们多喝开水,让伙房做了面条给端过来。感觉稍微好了点,我们就又上了工地。平时,我们这些知青一顿只吃一个或一个半馍。那年冬天,我们一顿能吃4个馍(一个馍2两,两个拳头那么大),但饭菜没有什么油水,撑不多久就会感觉又饿了。大家见面时都说很累、很困,但是没有人提出不想干。我们青年队的知青是坚持把活干完后,才回家过的1975年的春节。
也正是通过1974年的夏收、秋收两季锻炼,加上这次整修大寨田的重体力劳动的磨练,我们知青的思想品质和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什么苦呀累呀、土呀脏呀,根本不在话下。我们与广大社员真正地融合到了一起,基本上是他们能干的,我们照样能干;他们能吃的苦,我们照样能吃。
三、出牛圈的尴尬
1974年6月的一天,按照三队队长卢影常的安排,我和程胜利在生产队的饲养圈里出牛圈,也就是把牛圈里的牛粪和土挖出来,用作上地的积肥,再填进一尺多厚的新土。
我们二人一人出一个牛圈。把牲口牵出来以后,拿着铁锹进到牛圈里,挖一尺多深的牛粪和土,挖一铁锹就用力从后边墙上的洞口甩出去。一开始还可以,干了一个多小时后就感到胳膊酸痛,加上牛粪臊臭难闻,就出来歇一会儿,换换气。我们在外边换气的时候,碰巧被卢影常看到了。卢队长不酸不甜地讲了一句:“人家一个人一晌出一个,记3个工分,你们两个干到现在了,还没干完一半,这可咋弄哩?”说得我们很没面子。于是,我们又硬着头皮进去挖粪。
我们俩虽然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壮小伙,但是由于以前缺乏体力锻炼和经常性劳动,所以累得够呛。等到把活干完,其他社员早就吃过饭休息半晌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,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:我和胜利牵着牛,赶着骡子进饲养圈时,那匹高大的骡子就是不好好进去。我恼火地朝它屁股上打了两下,没想到它尥起蹶子朝我踢了过来,一下子将我掀翻在地,疼得我好大一会儿才缓过劲来。
当时就记得,这3分真是难挣啊。又脏又臭,又累又险,浑身上下都是一股牛粪味,一出气,好像连嗓子眼里都有臭味。回到青年队端碗吃饭,我拿着筷子,还感到手直打颤。
四、装窑与出窑
在我们生产队的西北,有一座砖瓦窑。平时有两个壮劳力在那里干活,负责挖土、和泥、拖砖、晾晒。凑够了一窑的砖坯以后,队长就带着我们去装窑。一二十个人排成一排,从砖坯子跟前一直排到砖窑里面,一摞砖、一摞砖地接力传递,装到窑里。这可是个重体力劳动,一窑可以装5万多块砖坯,一块砖坯有六七斤重,一摞砖坯有七八块,从搬运传递开始,一摞一摞地往前走,任何人都不能停顿。胳膊和身子不停地扭动传递,不一会儿,就两臂发胀,浑身发热,再过一会儿就是满头大汗,把我和席中原、程胜利累得可是不轻。再看看身边的社员,好几个都是满头大汗的小媳妇或大姑娘,还有几个是五六十岁的人,我们虽然累,也不好意思说什么,硬挺着干到收工。晚上躺到床上一觉睡到大天亮,半夜有尿硬憋着,根本不想起来去厕所。
等到出窑时,窑内的温度还是不低,进到窑里面就像走进了蒸笼,红砖拿在手里还略微有些烫手。我和席中原、程胜利负责一辆架子车,连装带卸跟着大伙出窑。刚开始还好,越往窑里温度越高,砖垛码得越高,卸砖装车就越费劲。手套破得不像样了,只能徒手搬砖装卸,两手都磨得破皮渗血。可是身边的社员们没有一个是戴手套的,都是徒手搬砖装车,一刻不停地干活。看着他们黝黑粗实的皮肤和满手粗糙的老茧,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农民劳动的艰苦,体会到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和知青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。
五、两碗捞面条
记得那是1974年5月的一天下午,我正在三队的麦场上和社员们一起晾晒麦子,二队的知青闫玉喜过来找我。
看见他愁眉苦脸的样子,我就问:“怎么了,有啥事?”他说:“我想家了,你和我一块回家吧!”我说:“现在不行,等干完活再说!”他就在旁边等我。等到收工,天都快黑了。我就问他为啥想回家,他说每天干活太累,不想干了,想回去。我劝他我们刚来还不到一个月,回去不合适。他两眼含泪说:“我心里可难受,就是想回家!”我一边走一边劝他,走走停停,停停说说,等我俩回到青年队时,伙房已经关门上锁了,做饭的王师傅已经下班了。
小喜一看没有饭吃,就又哭了起来。因为不知道王师傅在哪住,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,我就说:“没有饭了,不吃中不中?”小喜不愿意,说:“肚饿了,不吃心慌!”小喜比我小,我不忍心看他伤心落泪的样子,就说:“俺队砖瓦窑有个煤炉子,有锅碗瓢盆,咱去哪里找饭吃吧!”
小喜跟着我,顺着小路摸黑走到三队砖瓦窑。“老党”(因为他是个党员,所以社员们都这么叫他)见我俩过来了,就问:“你们俩这时候过来干啥?”我说:“我们俩因为收工晚,回到青年队伙房锁门没饭吃了,想找点吃的。”
“老党”看着小喜问:“你这孩儿咋哭了?”小喜说:“肚饿,没有饭吃!”“老党”一听,说:“你俩等一会儿,我去给你们和面擀面条。”
“老党”在屋里忙活擀面条的时候,小喜坐在外面凳子上直掉泪,很委屈地说:“这要是在俺家,俺妈肯定不会叫我干这活,早就把饭端到桌上了。明天咱回家吧?我真想家!”他边哭边说,闹得我心里很难受,突然感到很想家,也陪着他掉起了眼泪。
过了一会,“老党”端过来两碗捞面条。因为没有菜,他就用蒜臼子砸了两头蒜,放到面条里搅和着吃。我们确实饿坏了,端起碗三下五除二就吃了一多半。“老党”一看这阵势,就慌着又去下了一锅,不一会又端来了两碗。不知是高兴还是痛苦,是感激还是委屈,我们俩边吃边掉泪,端着碗再也吃不下去了。“老党”两眼直直地盯着我们俩,一声不吭。在我们俩离开砖瓦窑,走到路口向他挥手告别时,他大声说了一句:“孩儿,肚饿了再来啊!”心里忍着难受和憋屈,又怀着对“老党”的谢意,我们俩在回青年队的路上,谁也没有再说话。
回到青年队,大家都急着问:“没见你们两个吃饭,去干啥了?”程胜利和席中原见我和小喜不高兴,就问:“咋了?”小喜说:“我想家了,想叫林春和我一块回家。可回来晚了,差点没饭吃!”说着又哭了起来。胜利一看小喜哭,就说“我也可想家”,眼泪也掉了下来。旁边的高树房、席中原等好几个同学也跟着哭了起来,越哭声音越大。不一会儿,旁边的女生宿舍也传出了哭声,而且不止一个人,就好像是受了感染似的。大家都有个共同的感受,就是下乡快一个月,确实想家了。平时不想说,也不敢说的,在那个晚上借着小喜的一哭,大家终于憋屈不住,都哭了起来。
六、一条洗脸毛巾
1974年5月的一天早上,队长卢影常安排我去找社员卢广义一起往地里送肥。因为需要用架子车,我就扛着铁锹到他家里找他。那天他起得有些晚,正蹲在地上就着脸盆子洗脸,见我过来了,就招呼我坐会儿等他。
他双手捧起一些水把头和脸弄湿,随手拿起一个洗衣粉袋,往手心倒出一点,往头上一抹就开始洗头,洗完了拿起毛巾擦头擦脸。就在这时,我看清楚他手里的那条“毛巾”,根本不是我们平常用的那种,而是一块白色粗布,看样子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,黄黄的、灰灰的。我正琢磨着这“毛巾”光溜溜的,能擦干净头脸不能呢,老卢喝了一碗水缸里凉水,拉起架子车就准备走了。我说:“哎,你还没刷牙呢?”他说:“刷啥牙哩,走吧。咱农村人可不像你们城里人早上刷牙,晚上洗脚。咱也不买牙膏,不买香皂,省出点钱买些油盐酱醋比啥都好。”他不经意间的几句话,噎得我好大一会儿没有回过神来。那时刚到农村不久,对这里的生活方式和民俗习惯不太了解,所以不知道我是问对了还是说错了。
我们俩拉着架子车一直往前走。他看我不吱声,就说:“可不是我一个人不刷牙,村里边的人大部分不刷牙。牙膏、肥皂都挺贵的。”我问:“那你们身上脏了在哪里洗澡?”他说:“在家里用井水撩着洗洗就行了。”我说:“冬天咋办?”他说:“不洗!谁还专门为这跑到城里花钱去澡堂洗澡?”我们俩边走边扯。
第二天早上,端着脸盆去洗脸,看着手里拿着的牙刷、牙膏和毛巾、肥皂,我愣神想了很久,真的不知道该咋用了。
七、夜里引水浇地
1974年10月,地里的玉米长出来了,由于天旱无雨,苗儿耷拉着脑袋,急需要引水浇灌。
一天晚上,队长卢影常叫我和三队社员卢小窝一起,去离村三四里外的小郭富村水口引水浇地,说是晚上8点要准时把水接过来。卢小窝比我年长几岁,以前浇过地,比较有经验。他专门告诉我:“别看白天天气比较好,到了夜里天气很凉,你把衣服穿得厚一些,身上带点干粮,下半夜肚子饿了就吃点。”
吃过晚饭,我们俩就拿着手电筒,扛着铁锹,顺着土路和水渠走到小郭富村水口,在那里见到了公社管水利的干部老李和小郭富村的两位社员。在老李的看管下,8点钟准时将流往小郭富村的水口堵住,把流往塘石村的水口扒开。涓涓的河水,顺着水渠哗啦啦地流向下游,我们俩跟着水头一直往下游走。凡是有堵水的地方,就赶快清理干净,有漏水的地方,就挖土堵好。水渠的质量还算不错,水头也不小,一直往前流着,很快就到了我们三队的地界。按照队长事先的安排,我们俩先将北地的“谷沱”(水池子)蓄满水,然后挖开水渠的分水口,让水顺着地势浇地灌溉。
农村的夜晚静悄悄的,旷野里没有城市的满街灯光,也没有城里的喧闹。田野里传来蛐蛐的啼吟,“谷沱”旁边传来青蛙“咕哇咕哇”的叫声,不时有夜鸟从树上发出几声鸣叫。我和老卢打着手电,拿着铁锹,顺着一块块玉米地跟着水头引水灌溉。由于地势高低不平,有的地块浇得比较透彻,也有的浇不到多少水。忙到后半夜,老卢躺在地头睡着了,我打着手电继续看水。
皎洁的月亮挂在树梢。苍穹辽远,大地安宁。这份宁静让我对大自然充满了好奇和遐想,对农村生活产生了某种爱恋。卢小窝睡了一觉后,起身查看浇地的情况,看到一切正常,就招呼我也躺下来睡一会儿。我因为没听他的话,穿的衣服比较单薄,又担心地上有蚂蚁或虫什么的爬到身上,就坐在地头,一直挨到月亮渐渐淡去,东方微微发亮,林子里的鸟儿开始吵闹,远方村子里传来鸡鸣犬吠。
八、文体生活与学习教育
我们塘石下乡知青的文体生活是多种多样的。只要有时间、有条件,我们就经常开展文体活动。林萍、樊月芳在学校是排球队的,原永生、连明是篮球队的,张志明是乒乓球队的,常小凤自幼跟随父辈练习绘画。学校在欢送我们下乡时,专门赠送了篮球、排球、足球各一个,乒乓球、羽毛球各一套。大家又从家里带来或购买了二胡、月琴、竹笛、小提琴等。在青年队大院里,同学们利用集中住宿的有利条件,只要有空余时间,就互相学习,相互交流,既丰富了精神生活,也促进了与农民群众的关系。可以说,青年队成了塘石村的夜生活俱乐部。
大队支部书记卢庆隆和带队干部刘启运,在农闲时多次安排社员和知青们一起平整场地,修建球场,还制作了篮球架、篮球板、乒乓球台等。尤其是带队干部刘启运,先后带领我们知青到梨林公社的南程、思礼公社的荆王、克井公社的青多等知青点交流学习或进行体育比赛。林萍、樊月芳、原永生等还被推荐集训,代表济源县参加体育比赛。有绘画特长的常小凤,几乎承包了队里的文化宣传任务。她制作的壁报、板报,成了社员群众喜闻乐见的景观,受到过领导的表扬。
那时,农村三天两头停电,为了便于夜晚看书学习,同学们就自制了多盏煤油灯,或买上几根蜡烛备用。晚上,我们通常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看书学习,希望以后能够参加高考,做一个真正有知识有文化的人。老支书卢庆隆为了增强本村学校的师资力量,专门抽调冯爱清、原永生等同学到村里的学校任教,并安排我们回城里的学校,借一些图书回来。常小凤、卢素云等同学之所以能够在国家恢复高考后,顺利考上大学和中专,就得益于在农村不间断地学习和同学们的帮助。知青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思想品质的养成,则得益于老支书卢庆隆和带队干部刘启运的跟踪教育和严格要求,得益于社员群众的言传身教和关心帮助。
九、收获
在塘石,我们这些天真无邪、单纯幼稚的知识青年,有过梦想与希望,有过迷茫与惆怅,有过吵闹与愤怒,也有过理解与谦让。在塘石大爷大叔们的指导下,我们学会了犁地种地。在大娘大婶们的帮助下,我们学会了洗衣做饭。在大哥大姐们的言传身教下,我们学会了接人待物、应对困难和生活自立。
5年多的生活磨炼中,我们遵纪守法,没有出现与社员群众打架斗殴闹不团结或毁坏公私财物、偷鸡摸狗的行为,没有一人受到违法违规处罚,未出现男女之间伤风败俗的行为。在大队党支部的关怀照顾下,在带队干部的帮助教育下,我们26人中,有1人入党,2人入团,3人担任生产队副队长、妇女队长,2人担任现金保管员或实物保管员,有12人次出席济源县、新乡地区劳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,包括我在内,有5名知青应征入伍,2名知青考上大中专院校。青年队的索玉闽和常小凤、高树芳和冯爱清,在劳动中互相关心,互相帮助,最终情投意合,结为终身伴侣……
所有这些,也许是我们这批知识青年在塘石村受到好评,或者说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仍对塘石村念念不忘的原因所在。
(本文刊发于2024年8月8日《济源日报》第6版,作者张林春,1956年10月出生,中共党员。焦作市第三中学1974届高中毕业生,1974年4月至1976年2月在济源县克井公社塘石大队当知青,1976年3月入伍,1985年11月转业,先后在焦作市公安局山阳分局、车站分局、刑侦支队工作,历任派出所所长、刑警大队大队长等职。)